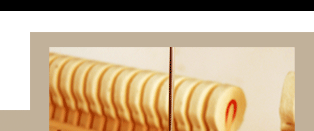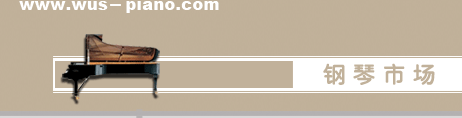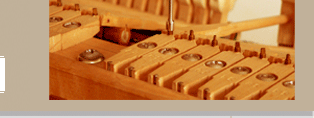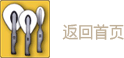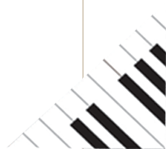狮城的琴行
沧州市区的琴行并不算多,但对于它的面积而言却并不算少。最早的一家琴行大概要数狮城琴行了,不过在三年多以前它已解体,并由一位股东创办了而今的天乐琴行。“天乐”主营北京钢琴,与琴行一体的天乐音乐学校秉承了“狮城”的教学系统,在琴行教学方面相对成熟。同样主营钢琴的琴行还有“政兴”和“海梅”。其中,海梅还主营电子琴。
和其他城市一样,吉他类的乐器在沧州卖得也不错。“骑士”、“木子”和“摇摆”这几家店面都是主做吉他生意的。“摇摆”是个后起之秀,一年三至四场的摇滚音乐会,他们已经主办几年了,在乐队迷中间是比较有名头的。
各种乐器经营兼顾的琴行有“永发”和“天喜善”。“永发”从20平米的店面开始起步,几易其地,现在已经拥有了约600平米的店面。“天喜善”开业不久,但是依托于市文化艺术中心,在教学上已经是蒸蒸日上。
“品牌”的力量
沧州人比较看重“品牌”——在许多琴行都能够见到“品牌”的“鉴证”——各种音乐类比赛的获奖证书、厂家的授权铜牌种类繁多。琴行任课老师的获奖证书,在琴行学习的学生参加各类比赛的获奖证书,上面标明的比赛有地区级的,有市级的,也有跨省的,甚至还有香港的“国际比赛”,大多是复印件,张贴在店内墙壁上。花些心思的,会把证书做成一个个的小展板,放在专门的地方。更有一位来自市内某文化单位的琴行老板将自己的获奖证书“真迹”横排一行,贯穿了一面墙壁,有的证书上的红印章竟有十来个。
厂家的授权铜牌也是随处可见,大多一拃见方,立在钢琴上。也有悬挂式的授权铜牌,大小一般是悬挂在单位门口的,此刻悬挂在店内。在一家琴行内,我竟然见到了大约20块这样的铜牌排列整齐地挂在一面墙上,让我感到震惊。
除了上述获奖证书、授权铜牌,“名人品牌”也是随处可见,大多是店主和社会音乐名人的各种合影,张贴在店内。如上种种,沧州人对品牌的看重不说自明。
听一位商家介绍,沧州有些乐商张挂的“授权铜牌”并非来自厂家,而是“自我认证”,我想这应是“有需求就有供给”规律在沧州人看重品牌这一现象上的体现吧。
身处大京津地区的尴尬
依据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沧州应划作“大京津地区”的范畴。沧州琴行的发展得益于临近的京津二市,但更多的是承担一些大城市带来的尴尬。
多数的琴行都会有到北京或是天津的琴行抓货的经历。规模小一些的琴行,无法要求厂家供货,尤其是吉他效果器这类需求量并不算大的商品。从北京或是天津的琴行抓的货的利润就非常的薄,这使大家苦恼。
但这还不是最深的痛——很多乐商都告诉我,尽管他们有非常好的商品摆放在店内,还是会被许多人只当作样品。顾客在这里转转、看看,然后就会跑到大城市去购买。一位店主告诉我,有一位顾客曾找他修一款雅马哈的电子琴,这款电子琴是顾客从石家庄买来的,同样的货色在那里要贵上近五百元,再搭上时间和路费,所费可想而知,顾客却心甘情愿。而这种现象对于吉他零售而言就更普遍了。
是这座河北省省辖市没有给其所现辖的10县4市2区和2个管理区内677万人口中的乐器消费者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支撑?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类似沧州这样规模的城市的乐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需要得到来自大城市的一种肯定?就如同这里的乐器销售者的销售心理需要来自各种权威的一种肯定?——我不禁想到店主们和社会音乐名人的各种合影。
消费力在哪里?
每个和我交谈的店主都坦诚地告诉我沧州的乐器消费水平,同时也会向我询问其他地区乐器消费市场的拓展方法,让我感到这些经营者的兢业。
乐器经营要和教学挂钩,这是乐商们的共识,“天乐”就是这样稳步发展的,“天喜善”也是这样在短时间内崛起的。但是如何确保生源呢?一位店主认为:“天喜善”的短期崛起与其邻近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密不可分,附近乘凉避暑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接触到“天喜善”,但是由于它邻近市郊(西环),相对偏僻,所以琴行规模很难扩大。
是不是地处市中心、毗邻商业区就会确保很好的生意呢?“海梅”曾在华北商厦中经营,后来易地在小区住宅楼内。自己购房的店主说,这样可以避免租金的困扰,继续经营大品牌。
一些店主认识到了“规模”对于消费者心理的影响,但是“租金”汇同“消费能力”的压力使得不少琴行在“规模”问题上裹足不前。许多价位高一些的乐器都需要预定,一位卖吉他的店主说,经常有人一进店就问“有没有假Fender?”——沧州人的承受价位到底是多少?每个人心里都这样问。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大家会不会灰心呢?——
一位商家告诉我,尽管早些年他进的Ibanez吉他一直“搁”在手里,但是今年却卖得很好。他说,可能是因为最近的Ibanez的用料不如从前,所以大家看出了“老”乐器的好;另一位商家告诉我,电子琴的销售低迷了几年后,今年又开始抬头,可能和最近“英语热”的降温有关;还有一家老琴行正在寻地扩大规模……无论怎样,这些都应算作是好消息!——沧州自有商业规律,只是有待发觉。这座没有被太多商业手段污浊的城市,总会发掘出自己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