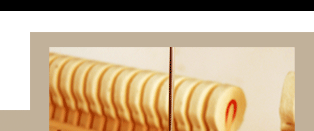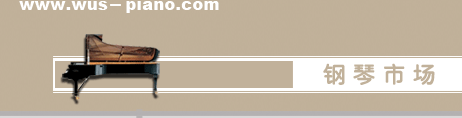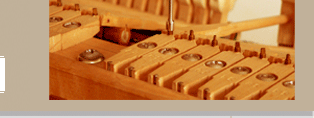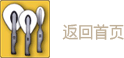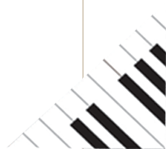9 月末,我有幸随国家轻工业乐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赴德清检测、调研。
刚下火车,我们就被早已等候的德清 质量监督局 负责文化产业方面的工作人员用车直载到德清钢琴文化馆。这个 6 月份刚刚建成的坐落于德清文化园区之内的文化馆,用摆放整齐的 30 余台钢琴迎接了我们。等不得茶水上好,负责钢琴工作的邱欣建主任就忙不迭地向我们介绍起这个文化馆来:钢琴展区,历史回顾区,音乐厅,会议室,休息区,还有一间小小的餐厅。我感受到邱主任对钢琴发自内心的喜爱。当晚,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大师、教育 家杜泰航 教授飞抵,专程前来配合我们做主观评定的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主体工作围绕文化馆进行,直辐射到洛舍镇乡间的工厂。在工作过程中,我看到了一幕幕让人意想不到的画面,由此也感受到了德清人对钢琴的执著与纠结。
精神的高度
德清的钢琴厂主几乎无一不是农民,德清的钢琴却大多有着外国名字。最多的是不知来历的德意文字拼写的品牌,最具特色的是汉语拼音方式拼写出德意发音的品牌。 杜 教授随机问了几个品牌的读法,厂子的技术人员们也搞不懂自己品牌的确切读法,甚至品牌的拥有者——工厂老板读起自己钢琴的名字来也是一幅不敢肯定读法的样子。搞得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围观的其他老板都偷偷地笑。
这些读不出自己品牌名字的老板,在精神层面却达到了一个高度,他们为“我的钢琴为什么比不上外国钢琴”挠头,虽然找不到原因,但却知道问题的答案在欧洲,虽然没有能力搞懂原因,但却知道欧洲发音的名字代表着品质。
品牌最响亮的是以音乐家的名字命名的品牌,以及音乐家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虽然在技术方面,老板们大多是小学生水平,在音乐家典故方面他们完全是音乐发烧友的架势。聊起这些音乐家或者他们的恋人来,老板们如数家珍。某些资格老、资金强的老板还会关注到音乐家名字所代表的风格、行事作风、艺术影响力。他们选择代表自己理念的音乐家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品牌,在所出口国家遇到品牌已被注册时,他们会把音乐家妻子(也是音乐家)的名字也注册成品牌,然后销售过去。当农民钢琴厂主用音乐家家族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品牌家族时,你还能说这只是一个农企附会名人的轻薄之举吗?
相得益彰
做主观评定时, 杜 教授认真地试弹每一架钢琴,厂主们松散地围在附近,等待评价。某一品牌受到点评时,其余品牌的厂主们会细心聆听,然后交头接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相互间交换意见。一开始, 杜 教授十分不适应:琴好还行,要是琴有问题,当着这么多人讲出来,老板多没面子啊?直到老板们接二连三地表示“就是要你挑毛病的”,“ 不用夸的”,“面子不重要”, 杜 教授才逐渐适应这种方式。这是平日罕见的一幕,表明德清的钢琴厂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方方面面。按从业人员来讲,德清的很多钢琴厂老板都是“搞”木头出身的。钢琴厂老板中有些是木匠出身,看到别人做钢琴了,也开始做。有的木匠徒弟要学,他们也不保守,教会了就又出来几个钢琴厂老板。还有些钢琴厂老板是做木材生意出身的,比如说木皮,本来是出口日本的,后来日本的订单少了,就开始改作钢琴了。洛舍镇工业副镇长徐畅的名片的背面有两行字,“木业重镇 钢琴之乡”,说出了德清钢琴的这个特点。因为德清的钢琴厂大多地处乡间,大多数人最早是农民,因此有了“农民造钢琴的说法”。如果捋捋关系,这些个老板全都“串”得起来。
按产品来讲,虽然德清有近 50 家钢琴厂,但是产品线却很容易归纳。看看他们的铁板就知道他们中的哪些厂在共同仿制某一经典型号,或者有着共同的供货商;看看他们的机芯就知道他们中的哪些厂订的是一家的货。也许有人会简单地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抄袭”,我却认为这是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对技术上的一种追求。“设计”、“ 制作”等这些软性品质无法在短期内提升,他们就在硬件方面做了最大的付出与尝试。“ FFW 毛毡”,“红木槌芯”,这样的配置早已超过了大多数 yamaha 钢琴甚至是欧洲钢琴。只要周围有厂用过并且觉得好,就会马上被跟进,并且直“跟进”到“同一家”供货商。
近 50 家厂麇集一县,竞争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但大家确又相安无事,不但相安无事,还互相下订单,互通成品琴或者配件,“相得益彰”这就是德清钢琴产业的特点。
老板的烦恼
老板之间相得益彰,老板和工人之间可是一言难尽。在餐桌上,老板们对我大倒苦水。
“ 吴 老师,那个马钉的角度,你讲的很对,我们也想抓好细节工作,可是工人不管,只知道马钉敲进去就好。你不能说他,一说他就走了,连招呼都不打,工资还必须给。比如一个工人一个月开 4000 块,工作 28 天,他加班了你必须加钱,他犯错误了,不能罚款的,罚了他要‘告'你的。”
“怎么做你要教他的。我嘛就示范给工人看。幸好我会木工啊。老板要是不会就完了,工人会说‘你来做啊'。音板没做好要报废,要我自己修修好,否则让工人修是要计件的,如果不计件他要不高兴的。他把音板做坏了要我修的,如果让他修还要计件给钱。”
“示范给他看?我还要请饭呢。我那里有个 15 年的老工人,做铁板的。钻孔总是有问题,向你说的那样不均匀。下了班我要请他吃饭,还要给他点烟,请他以后注意一下。结果是照旧啊。 15 年了,我也不能请他走啊,我呐就把一部分铁板委托铁板厂钻孔了。他那里是数控的,可以全部做好给你。可我还不能都这样做,我只把一部分给他做。原来工人要做三块板,现在只要做两块,另一块铁板厂给做好了。我就放在那里给他看,人家的孔钻得多好。你要是再不改,我就让厂子做两块,你做一块 …… ”
“我也要自动化,可是工人不干啊。自动化可以,不可以减工资。他干的比以前少,可是工资不能少的。我只能再招新的工人,让他们用电动工具。”
“音板的工人不好管啊,说走就走。上次那谁有 100 个琴被退,全部是音板马钉浮起来了。运费 1000 块一台,往返就算 800 块一台,这一下子损失多少啊?”
“你不能什么都交给工人的。他不会管你哪里要换钻头、换螺丝的,他只要钻下去。我每天早上到厂子先要看是该做发给哪儿的货了,然后他在那里干,我在这里把钻头给他提前换好,然后递到他手里 …… ”
“我那里有个工人把虎口割了,来找我要钱,‘村里人说了,这要赔钱的。'我去劳动部门问了一下,他们劝我赶紧赔,说要是告起来赔的更多。我就赔了钱。结果过了几个月,我在另一家厂看到他在干活,手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可是赔了好几万啊 …… ”
目前的劳动法对工人的保护多一些,给老板们的生产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使得老板们对工人有需求的同时“又恨又怕”。 “管理哪有那么容易?××厂从东北请了个技术人员管生产,才 3 天,工人就都不干活了,你怎么管?”
但是最近持续的市场低迷给老板们带来了一丝希望。他们说:“最近市场不是很好,工人们好像踏实多了,因为招工的地方少了,而且跳过去也不一定有这儿好。”
成本的较量
当然,德清的钢琴业圈内并不只是一团和气,商业上的较量是必然存在的。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大家可以拥有共同的供货商,但是这不意味着大家可以将市场拱手相让。他们的竞争有着德清人特有的温婉与坚持。比如,有老板在洛舍唯一一家像样的饭店的一层租下 1/2 的大厅做产品展示。“他是要让来这里吃饭的人都看到的,可这下子来这里请客吃饭的(琴厂)老板少了”,另一个琴厂老板告所我。
当然,最根本的较量还是在成本。沈有福经理给我算了一笔帐,组装、调试一台琴的人工成本是 400-500 元,如果音源、外壳是外购的,成本还要低一些。但是音源正是他“傲视”德清的立足之本,因此无法割舍,他准备剥离外壳车间,让企业轻装前进。有些企业从材料上入手,盯上了旧木料市场,“这样一来,一台琴可以从材料上降低 1000 块成本”。
不管多大多小的企业,都知道要减少人员的开销。鲍海尔经理得意地告诉我,他的厂子坐办公室的算上他才有三个人。很多企业,老板娘,甚至老板都开工,这是我初次所见。我们在考察配件厂时,陈小平厂长正在生产线上,是他老婆听到电话响从另外的生产线上跑去叫他,他才赶来见的我们。
还有些小企业,以来料组装贴牌为主,人员成本更低。有个厂是连襟 4 人合作,月产二、三十台。他们受行业波动影响最大。同行评价他们:就是挣辛苦钱,挣不到利润。但我想,正是因为德清人放得下架子,吃得了苦,动得了手,才成就了“德清钢琴”吧?
被关注的宝地
德清人对钢琴如此执著,外面的资金也开始注入。
一些若有若无的不祥气息被敏感的厂主嗅到了。据说新的投资者里面有从上海淘金而来的。当时此人是在厂里做销售,勾结某地的琴行主付定金下订单。厂子为此生产了大量的非主打型号。在行将交货的时候,琴行解除了合同。厂子虽然收取了少量的定金,却因此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样压货半年之后,又有一个琴行主来厂子考察,“无意”间看到了积压的钢琴,于是提出低价买进。厂主为了解套,只得低价出售。如此一个往复,原来的销售“发”起来了,又盯上了德清这块宝地。
更积极的是珠江的资金注入。 2003 年 9 月,合资成立的“珠江德华钢琴有限公司”形成各式钢琴及外壳配件等 30000 台套的生产能力。从此,德清洛舍镇成为继珠江之后的全国第二大钢琴制造基地。
技术的迷茫
外部环境影响不了钢琴带给德清人的正能量。他们一如既往地将汗水洒在钢琴事业上。有了好的品牌拼写,有了固定的客户订单,他们还要持续的技术发展。在检测过程中,有好几位厂主拉住我指着某些厂的琴问我:我和他用的东西都一样,怎么声音不一样?这是企业使用了“ FFW 毛毡”,“红木槌芯”之后声音效果仍然有缺陷带给厂主的烦恼。烦恼依旧,奋斗依旧。
由于德清地处江南,必然地,钢琴生产制造技术受到上海、宁波,甚至广州的影响。大厂采用的操作手法这里也有,只不过更随意一些。大厂采用的管理方法这里也有,只不过更细碎而不成体系一些。从同一个地方进货是这些厂主对技术的初级追求。高级追求就是聘请技术人员。能力强的,聘请大厂的知名技术人员;能力有限的,聘请大厂的不知名技术人员。伴随在这二者之间的,是自主的设备改造。大厂所能见到的自动化设备,在这里也能见到,只不过没有那么普遍。更多的是大设备的简化,或者具体工序工具的自动化 / 半自动化。没有那么气派,但却绝对实用,绝对的高性价比。同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面,他们努力“拷贝”着世界顶级钢琴。某厂仿照 Mason & Hamlin 的蜘蛛背,做成三角琴的一体木背柱,某厂仿照 Steinway 做成了“孔雀”三角,更多的厂在仿照 Yamaha 的主体结构。
当然,虽然企业付出了很多,产品也还是存在着某些问题。此次检测中,我们在技术方面共发现五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机械回落噪音偏大,高音区的轮指连贯性不好(键回升负荷),制音器与踏瓣的调整关系不好,旋律无法流畅弹奏(制音器开启时间)及音准不好。前两项问题通过设计或者管理人员对生产的调整即可解决;三、四两项在管理人员明确调整原理之后对具体工人强调调整数据或采用工装即可解决;最后一项,一时难以解决。不过,音准的问题决不是德清独有的问题,国内的大厂也多存在这一问题,与其说是从业者的素质问题,不如说是管理者的理念问题。在日本或者韩国,流水线钢琴生产早就采用了仪器调律这一使音准相对一致、相对稳定的方式,中国的大企业尚且拒绝,德清出此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是不是德清的钢琴就是差琴的代表呢?并不是。根据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检测结果 和杜 教授的主管评测来看,总体上德清钢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用 杜 教授的话说,虽然有的琴“琴挺大,但装不下乐曲”,但是个别在德清钢琴里并不起眼的小品牌 却让杜 教授“能将乐曲同时弹出四个层次”。这在国产立式钢琴里面是很让人吃惊的了。
钢琴企业的历史位置
在这纷杂的表象之后,德清的钢琴企业有着绝大多数中国钢琴企业共同的“痛”的历程: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问题在哪里,不知道怎样解决——知道问题怎样解决,不知道如何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知道如何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却无法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这是由于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虽然德清农民在精神层面上超越土地的束缚直抵上层建筑具象化的钢琴,在物质的生产层面却无法超越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想来,这也是全部中国钢琴企业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