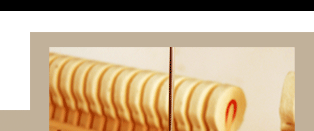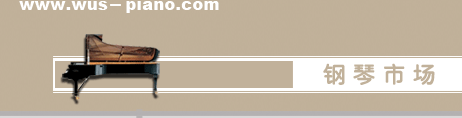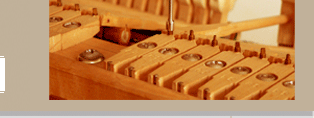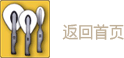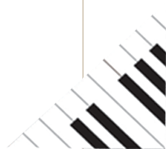颇具影响的“乐商”
浙江自古文人画客层出,文化氛围浓厚。宋王朝南渡杭州,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近代,浙江又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出国留学者众;同时,外国资本主义渗入导致了包括意识形态的种种变化,使得该地的商业活动很是发达。这数百年的“商”与“文”的深层交融,使其地的商业活动极具文化特点。杭州,作为浙江的首府,更是这种交融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风气”连带得杭州琴行的“掌门人”大多专业水平较高——
广安琴行的经理陈余是浙江交响乐团的成员;之江琴行的经理虞晓江是杭州师范大学的音乐教师;三毛琴行的经理蒋淳荣(被大家称作“三毛”而广为人知)原是杭州歌舞团的专职调律师;天目琴行的经理刘为明曾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专职调律师;幼师琴行的经理董永常现在还是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的专职调律师……我们常用“儒商”一词来描绘带有浓重中国传统儒家风范的商业精英,如此看来,杭州琴行的各位“掌门人”可是不折不扣的“乐商”了。
这些乐商带着南方人特有的温润态度,即便在评述竞争对手的不是时,也是脸上永远挂着友好的微笑、说话温和得体。他们随和得更象是一些“邻家大哥”,却打造出了拥有近50家连锁经营店的,号称全国最大的琴行——“天目”;主店面积仅48平米的珠江钢琴销售大户——“三毛”;“雅马哈”萧山特区的授权琴行——“新世纪”;浙江电声、电子乐器最大经销商——“广安”……
杭州,并非直辖市,没有政策的“优惠”,也没有沿海城市的“便利”,乐器经销却作得如此有声有色,可能是因为他们“商”得亦“文”亦“乐”吧?
永远无法完成的“火并”
可能外人无法想象,取得如此骄人业绩的杭州乐商,是在何等竞争环境下生存并壮大的。杭州的城市并不大,琴行数目也不算多(据称有30家),“战火”却自1997年左右琴行“激增”开始点燃从未停歇过,而且手段之烈达到极至。
最初,仅是一些乐商在向顾客介绍商品的时候,贬低他家经销的品牌。随之,开始有一些乐商设法购入其它琴行主营的产品,标以低价,进行竞争。当口头的贬低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一些相互间竞争较激烈的乐商开始采取笔头的攻击,其语言之巧妙,方法之多样,使人想到“绍兴师爷笔法”锋利、深刻、善于击中要害的特点。自宋王朝将图书律令迁移绍兴,“绍兴师爷”的名气自彼时数百年不衰,如今虽然不再有“绍兴师爷”,却应时而生了“杭州乐商”。也许是因为杭州与绍兴比邻,同沐浙江文化,杭州乐商在商战中将绍兴师爷的“笔法”特点运用得如火纯青。他们有的在企业内部印制的刊物上评述其它商家的产品;有的在媒体采访时“不点名”评论别的商家(由于经营品牌划分较明显,实际效果等同于“点名”);有的干脆直接印制宣传品,上列他家主营的乐器品牌、型号和“虚拟”价格(当然,这些“虚拟”价格无疑又是一种攻击他人的手段)……
接着,一些较大的琴行,开始争取更多的品牌代理权,以便阻碍其它乐商在品牌上的扩张。当如此竞争导致利润急剧衰减时,一些乐商开始进行订牌生产,在牢牢“纂”住众多品牌经营权、阻碍其它乐商在品牌上的竞争的同时,推广自己的订牌产品,以获取利润。一些小琴行也不干示弱,和其它城市的代理商联合,取得价格优势,在某一类产品上(如某一品牌的电子琴等)向杭州本地大琴行“挑战”……如此近似于“火并”的商战导致乐商的利润普遍大幅下滑。据一位乐商介绍,在杭州的一次投标活动中,中标琴行的一架雅马哈自动演奏7尺钢琴,才仅仅挣了1000元。不少在其它城市做得很好的乐商进入杭州后,发出了“杭州(乐器行业)的竞争太混乱了!”的感慨。
琴行间的“火并”甚至影响到了工作的其它方面。基本上杭州所有的琴行都很重视媒体宣传,但是过分敌对的情绪使得电视台在制作音乐节目租用乐器的时候都感到了“火药味”。据一位乐商介绍,现在,杭州电视台不再从两家资历、矛盾都颇深的琴行,而是从另一家外来的琴行那里租用钢琴等乐器制作节目。
可是,如此“火并”的结果不是某家琴行消失了,而是乐商们发现——“谁也打不‘死'谁!”其后,不知何时起,乐商们似乎突然停止了“火并”,开始采用相对缓和的竞争手段,但是曾经的“火并”给市场留下的“伤口”不知道何时能“愈合”;曾经的“火并”给乐商留下的“阴影”不知道何时能消除?
乐器市场的“围城”
说到杭州,人们就会想到“京杭运河”。“京杭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其名始于明清,其成形却是早在隋代。据史载,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凿通江南运河,与江北运河相接,杭州由此成为通衢之地。作为承载千余年历史 “经济”、“文化”的运河一端的杭州,无疑是“经济”、“文化”的“集散地”。
现今,“京杭运河”的作用虽不如昔,可是浙江全省交通发达,作为浙江省的首府,势力辐射至整个浙江,杭州集散“经济”、“文化”的地位却更强了。身居首府,杭州的琴行很多都拥有某些品牌的浙江总代理权,而且很多都有分行(按照杭州乐商的习惯,他们将琴行的分支机构、加盟店或“下家”称作“分行”)象“天目”、“幼师”……主店40仅余平米的之江琴行在顶峰时期就曾有9家分行。各种品牌正是通过这些分行“散”到各地的。受杭州商圈的影响,这些分行把“战火”带到各地。由于浙江全省交通发达,同家分行之间有时甚至都会身不由己地卷入自相残杀式的商战。“天目”琴行为避免“内战”,特别采取了“同城异名、异城同名”的扩张手段,分行间“战火”的惨烈可见一斑。
为了应对商战,“天目”琴行开始跨行业经营,同时努力向环浙地区发展分行,以缓解竞争压力,并通过为员工提供股份,提高企业凝聚力;“广安”将经营重心由电声、电子乐器零售转向投标音响工程。萧山“新世纪”则是瞄准了“雅马哈”将日本滨淞“变”成音乐文化产业基地的史实,力图把本店所在地萧山打造成中国的“滨淞”,再通过杭州扩大自身的影响……
一些在其它城市的有一定规模的乐商,或是主动,或是在受到杭州琴行分行的“挤压”后,挑战性地将琴城开到了杭州。象温州的文海琴行、义乌的通远琴行等。其中,“通远”在浙拥有20余家分行。
外来的乐商使原本市场“拥挤”的杭州乐器市场竞争更强烈了。有的乐商想挤入杭州,有的乐商想冲出杭州,这就是杭州乐器市场的“围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