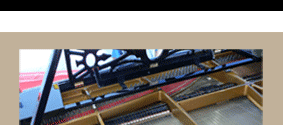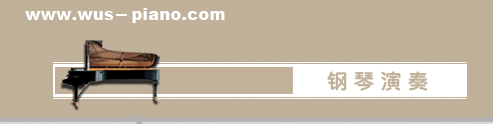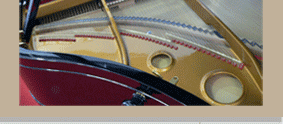丹尼尔·巴伦勃伊姆(Daniel Barenboim,1942-),以色列指挥家、钢琴家。
1942年11月15日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母都是钢琴教师,7岁首次举行贝多芬作品独奏会。
1951年随家移居欧洲,1952年定居以色列。同年获美国的以色列文化财团奖学金,至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先后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罗马圣西西里亚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随菲舍尔(E.Fischer)学习钢琴,随马克维奇(I.Markevitch)、布莱兹学指挥,师从纳迪娅·布朗热学习作曲。
巴伦勃伊姆10岁开始活跃于国际乐坛,先后在萨尔茨堡、维也纳、罗马、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等地演奏协奏曲,担任指挥的多为一时名家,包括克路易坦、克里普斯、斯托科夫斯基等人。
1954年在维奥蒂(Viotti)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
1958年获贝多芬奖。
1962年在以色列首次登台指挥,从此身兼钢琴演奏和乐队指挥。
1963年获帕德雷夫斯基奖。
1965年起与英国室内乐团定期合作演出,长达10多年,1969年曾率该团巡回演出。
1967年与英国大提琴家杜普蕾结婚。
1975年接替佐尔蒂(Sir Georg Solti)出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兼指挥,在职15年。
1982年获贝多芬学会奖。
1987年兼任巴黎巴士底歌剧院音乐总监。
1991年出任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兼指挥。一年后又兼德意志柏林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巴伦勃伊姆的钢琴演奏长于乐句的表情处理,对旋律线的表现能力很强。他演奏的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全集及他与杜普蕾、祖克曼合作的室内乐都获得很高评价。
改变了我生活的音乐
译自《BBC Music Magazine》2000年4月刊
我的父母都是钢琴老师,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单元里。每次门铃响时,都是有人来上钢琴课,所以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弹钢琴,直到我大到可以出门去看看了,才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弹钢琴,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搞音乐的,但音乐对我来说一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长久以来一直跟随我、并被我用来鉴定其它音乐作品的音乐是贝多芬的交响曲。由于在家里弹由这些交响曲改编的四手连弹,所以早在听到或指挥它们之前我就已经熟悉这些作品了,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11岁时由富特文格勒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指挥贝多芬第七、第八的那场音乐会,它改变了我以前感受和理解音乐的方式,尤其是第七的末乐章是如此不可抵抗。
1952年去以色列时,我作为独奏与指挥乔治·辛格合作演奏协奏曲。辛格是捷克血统,当时他在以色列以及欧洲的几个歌剧院很活跃,他对我很感兴趣。令他心烦的一件事是他不能指挥瓦格纳——因为不论当时和现在,瓦格纳的音乐都不能在以色列演出,但歌剧却让他非常兴奋。是辛格让我了解了瓦格纳以及他的管弦乐法,并由此把我领入一个新的领域:瓦格纳、李斯特等等。我尤其记得他的“齐格佛里德”。
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在我生命的一段时间里曾经非常重要——演出被录制成电视片,演奏者还有杰基(他的第一任妻子,大提琴家杰克琳·杜普瑞)、帕尔曼、祖克曼、梅塔。当时对我们来讲,这场演出就像是我们演奏音乐的一个标志,年轻、自由奔放、充满活力。我从来就没想过能再现那段时光,我不相信再现。事情发生时,人要有勇气接受并向前走。
另一首对我的生活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品是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音乐上的原因,因为当时我对埃尔加的音乐几乎毫无了解,当然是通过杰基,我对他的大提琴协奏曲产生了兴趣,但从那以后,我指挥演奏了埃尔加绝大部分作品,都是非常美妙的音乐,可惜这些作品在英国以外鲜为人知,我曾和很多优秀乐团演奏过他的作品,像柏林爱乐、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都是杰出的作品和演奏,尤其是第二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热爱。
鲁宾斯坦让我了解了肖邦。他开场常弹的一首曲子是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他高贵、宏大的演奏风格与当时流行的像患了结核病似的病态、感伤的肖邦演奏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宾斯坦的处理非常有阳刚气,他弹出了音乐的高贵与宏大,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
巴托克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对我很重要,这是我和布莱兹、也是和柏林爱乐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在那前一年,我和柏林的另一个乐团演奏一首协奏曲,柏林爱乐的经理邀请我和布莱兹合作,并说一定要弹巴托克的第一协奏曲,我试图说服他让我弹一首我已经很熟悉的曲子,但曲目早已定好了,所以要么就弹这首曲子,要么就什么都不弹。我当然是弹了,而且很高兴我弹的是这首曲子,因为自那以后我越来越喜欢它,和布莱兹多次合作演奏这部作品,它成了我们的聚会曲目。
|